從北捷踢人事件談優先席的意義與存廢
台北捷運於四天前(9/29)日發生「優先座(Priority seat/Courtesy seat)」爭座衝突事件,七十三歲曾姓老婦疑似不滿優先席被一位年輕女子佔據,而以內有盛物的提袋兩次甩向該名「女子」,欲示意對方起身,卻未料遭到兩次連續反擊。從影片中顯示,曾婦在公眾場合直接以提袋碰撞趕人起身的行為確屬失當且有傷人自尊與形象之嫌。而該位扮女的年輕男子受過一流學府教育,卻在自覺受辱後對高齡女性做出逾越比例原則的踹踢反擊,更屬不當的羞辱行為且可能造成老人無可復原的實質傷害。
這個事件顯示出:(一)優先席的意義,事實上與過去的博愛座並無差別,主要針對體力已衰退的老人群體、體格較弱小的幼童群體,以及身體有殘疾或病弱的人們。博愛座,顧其名即是從愛心與同情心出發,期盼大眾能支持此種社會美德。優先席,並非指先上車者就是優先坐者,而是隱喻相對輕壯健康者能讓位給那些更需要的老少弱者。就此次單獨事件而言,曾婦想坐門邊優先座而非其他空位,應有雙重意義,一個是吊掛物件方便,另個即是優先座本即以高齡者為優先而非年輕人,這是客觀事理。
除非年輕人身體病發難受或殘疾,則自然比身體無不適的高齡者更優先。同樣,相較老人與小孩,何者更優先,也得視雙方年齡與體況而定。通常,肢體力弱的幼兒可由家長抱坐,經濟利用座位。除特例外,大多數的現代健康兒童則可能比多數高齡長者更有體力站立,萬一跌倒時的碰撞傷害也大都比老人相對的輕,因為兒童的筋骨較具彈性與活性,復原能力也快。老人則相反,骨骼易斷裂且難以復原。這也可能是老人排在弱、婦、孺的前面要因。
其次,(二)是非對錯問題,即使曾婦適用優先席而對方不適用時,亦不宜以此方式強意對方讓坐,畢竟公眾之下的人均有一定自尊與形象之需。若覺不當,長輩可以低聲勸示對方轉移其他空位,不使其難堪而造成羞怒而衝突。特別是對那些格外重視外在儀表且打扮體面的人更宜謹慎措辭有禮,畢竟有時顏面自尊更甚於是非德理。優先席的設計本即老、小、病弱者優先,如果這些群體選坐了其他座位,等同將他齡健康者消極的趕往優先席去坐,那麼便易顛倒事理。
因就經濟理性而言,若任何一位高齡長者選坐普通席位,不啻等同同時佔據兩個位置,理由是大多數輕齡健康者並不會無由而選坐優先席,即使有空位在前。因為他們仍在意大眾眼光,仍講究社會規範與道德事理。反之,若老小病弱群體不選坐優先席,是否即意味鼓勵輕齡健康者也就不無須刻意迴避優先席? 此將反使優先席失去其本質、意義及事理,更攪亂了大眾對優先席的正確認知與應然看待。
年輕的扮女張男日常本講究優雅形象,為何此時逆轉為憤怒男? 扮女,除挑戰傳統性別刻板文化外,也是實踐陰柔美學的表現。但為何要選坐優先席? 除內在抵抗傳統教條外,可能也有保護自己的意圖,免受其他近觸與受侵犯的機會;特別是近來才發生「美少男于朦朧」遭性侵殺害的不幸事件;因此,張男選坐優先席自然能排除潛在的性別侵犯可能;但卻未料反遭女性高齡長者觸擊,不僅有損公眾優雅的自尊,還破除了其所以尋求更安全的相對弱勢者之優先席的本意,或許是在「奪刀長髮哥」事件的暗示與鼓舞下,才選擇了在眾目睽睽下展示了其男性本有的反擊能力。雖損及自尊卻昭告了天下其不受侵犯的結果,同時也能帶來媒體關注的粉絲流量。
(三)優先席的存廢,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優先席確實有其存在必要,因為它維繫著當代所僅存淡薄的人際倫理道德,企圖保護所有的客觀弱者,以及類似張男的主觀認知弱者。只是性別裝扮完全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但優先座的本質卻非可以任意被界定,因其本有消極指定性,被限制為不可改變之特定客觀條件者的權利。在我們選擇了某種興趣卻帶有可能風險的行為之前,即應做好應對的自我保護與心理準備,而非是尋求外在保護那些無可選擇者的客觀措施。老化、幼小、天生病殘,都屬難以避免的自然現象;可避免的是非優先者們的自我健康維護。如果非優先者因個人常疏忽健康而常坐優先席,此合理嗎?
老化及幼小是人的自然生理變遷現象,任何人都必然經歷。設立優先席並無不公平之處。若一個人還坐不到,總有家人長幼者能享此權利。因此這是一種講究平等的特有權利,非僅客觀上照顧到長幼及行動不便者的公平而已,還兼顧了那些主觀上病弱的非優先者,故本文認為優先席宜值維續。所應求改善的是國民的心理健康,公共禮節,溝通技巧,媒體報導視角及素養,以及我們的適齡體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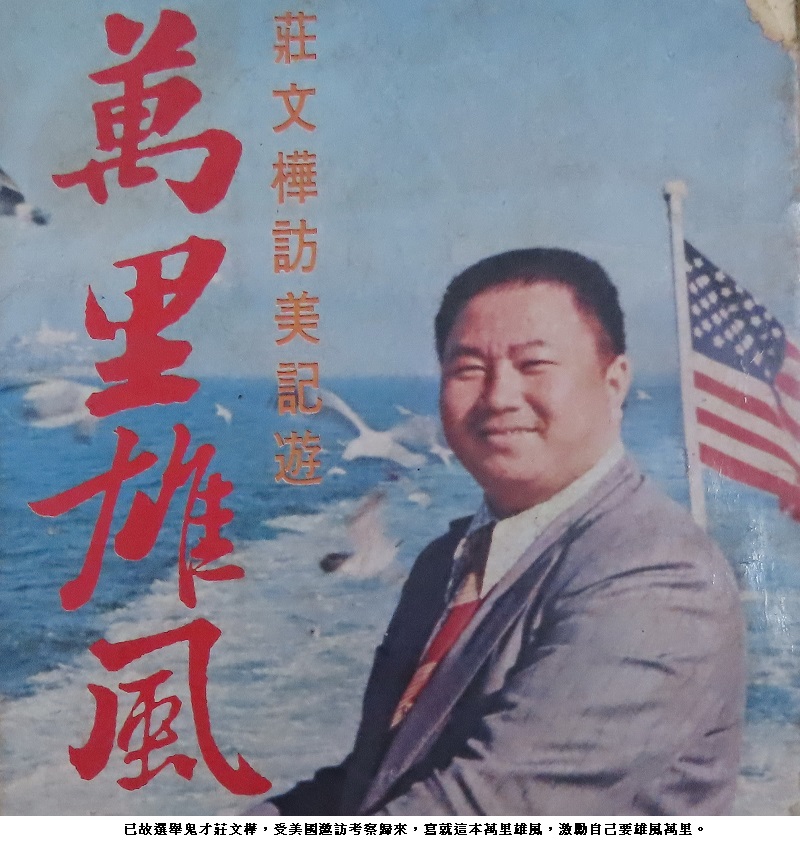











 Line
Line
